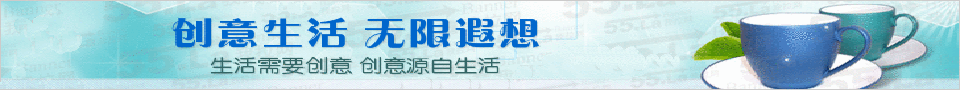

柳湾人像彩陶壶
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1974年,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墓地的考古工作中,采集有一件十分罕见的彩陶壶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年,央视四套的《国宝档案》节目,曾为它做过一集专题纪录片。然而,甘青地区的史前彩陶出土量巨大、纹饰繁缛、争奇斗艳,为何这件彩陶壶出类拔萃,格外引人入胜呢?
首先,这件彩陶壶属于彩塑一体,从工艺上来讲就更胜一筹。根据发掘报告的描述,器形为小口、短颈、上腹部圆腹、下腹部斜收、平底,最大腹径以下装有一对小耳。陶质为泥质红陶,口部至双耳上方施红色陶衣,绘黑彩。颈部为交叉斜线纹,鼓腹两侧绘有一对内填网格的圆圈纹,圆圈纹之间绘一简化的蛙人纹,或称“神人纹”。至此,无论器形抑或彩纹,均为马厂文化彩陶器之典型,常被用于墓内随葬。而此件彩陶壶与蛙人纹相对的另一面,尚可见蛙人纹中象征腿部的带爪折线,而原本的身躯部位却是一尊捏塑的裸体人像。人面塑于壶颈部,双目细小,上有黑彩绘出的眉毛,鼻梁尖挺,口半开,耳廓较大。身躯与人面不成比例,明显经过压缩处理,胸前有尖凸的乳头,乳头中部偏下似为肚脐,双臂环抱于腹部,肘凸出,五指分开,指尖相对处为夸张表现的生殖器官,双腿向外撇。乳头和肘凸以黑彩点绘,足部亦似有黑彩涂绘的痕迹。
史前时期的陶塑人像,在各地不同考古学文化中时有出土,不乏精品。但如柳湾彩陶壶这般,全身形像完整、刻画生动的作品,毕竟少数,而这一裸体人像造型夸张的生殖器官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第一次发掘简报直接将其定性为男性,并以此作为父系社会的证明,相反,也有专家的意见倾向为女性,分歧即在于其第二性征所表现出的特点有些“模棱两可”。李仰松将人像的臂弯解读为女性的乳房,认为其与胸前男性的乳头并存是两性复合的象征,反映出原始社会中的婚姻形态已出现一夫一妻制。但他仅仅认为生殖器表现的性别可男可女。而周庆基则认为人像的生殖器既有阴茎又有阴唇,象征着男女合体,他将此人像解读为“双性神”偶像,代表了祈求生育和丰产的原始宗教信仰。宋兆麟在《民间性巫术》 一书中,对“两性人”的讨论也使用了这一标本作为考古资料证据,认为是父权制逐步建立过程中,原始先民从崇拜女阴向崇拜男根过渡的产物。
客观上讲,如果不能明确地指出人像具有分属于男女的性征,那只能说明在今人眼中人像的性别模糊,而并不等于其设计之初就具有表现“雌雄同体”的愿望。事实上,此件陶塑人像的艺术风格偏于写实,性器官虽有所夸大,但还是能突显女阴的特征,反而与史前时期明确为男性阳具的艺术形象有较大的差距。至于其面部表情粗犷、双臂健壮有力的特点,对于性别的判断均无说服力。由于是采集品,此件彩陶壶脱离了原生的遗迹单位,失去了出土情境中保留的大量信息。比如,倘若用于随葬的话,与其他器物的共存关系如何?墓主是男是女?有无特殊的摆放位置?是否属于某些特定级别或承担特殊角色的个体?这些问题已无从回答。
然而,从彩陶壶本身来看,仍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宝贵信息值得提取。首先,鼓腹的壶身造型与躯体的配合,最易令人联想到妇女的孕肚。其次,人像的塑造代替了原本属于“蛙人纹”的画面,说明“蛙人纹”与人像应具有某种对应关系,而蛙则恰恰具有原始先民所崇拜的旺盛的生殖能力。第三,人像生殖器官的夸大表现,与身躯被压缩的做法形成对比,显然具有突出表现生殖器官的意图。如此看来,“生殖”、“丰产”、“孕育生命”应是柳湾人像彩陶壶最想表达的主题,其所反映的,应是柳湾先民对于人类自身的增殖或物产增殖的愿望。至于是否已经涉及对生殖过程中两性活动的关注、对男性在生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关注,则言之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