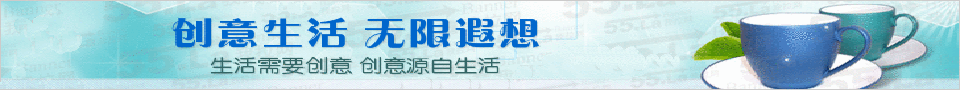

名导演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拍摄《意乱情迷(Spellbound)》时,配合正当令的“心理分析”风潮,请出了超写实主义画家达利(Salvador Dali)创造了几场梦境中的“奇景”,把男主角葛雷哥莱.毕克(Gregory Peck)从童年到成年期间,所累积难遣的心理忧结都设计了既奇特又让人费解的迷离幻境。
人生际遇难免起伏,压抑挫败情绪不时就会悄悄渗透进心灵之中,不足与外人道的压力往往就会遁入梦境,在那个触摸不到,醒来即忘的特殊时空中,却透露着个人潜意识里的期待与恐惧,因为有着人心防卫的刻意伪装与变形,所以幻化得光怪陆离,聪明的导演因而都乐于在梦境世界中打造意境丰饶,又匪夷所思的诸多意像场景。
做梦的人,其实必未能够理解梦境蹊跷,醒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反正不管是春梦、噩梦或乱梦,醒来了无痕,也就罢了;但是电影世界的梦,都不是意外的插曲,既创造了意境,更负担起解谜传薪的重责大任,一旦梦归梦,戏归戏,如此结构就让人觉得鬆散,“解梦”的功力与技法,因而成为电影世界的重要关卡。
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细笔描绘着思春女郎杜丽娘的春梦,书生柳梦梅让她一见倾心,甚至有了“忍耐温存一晌眠”的浓情厚爱,梦醒后自是“回首东风一断肠”的百般惆怅,不但有“寻梦”之举,甚至在“离魂”之后,还有“幽媾”、“掘坟”等癡情相缠的情节...梦与人生的紧密关连,构成了《牡丹亭》的主轴,也在“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绮丽文句中,激荡出中国文人的书香清梦。
《牡丹亭》相信的是“梦如人生”,有梦,就有人,才会癡癡缠缠,非得圆梦才肯罢休。电影中的“梦世界”也有着同样的信仰,梦中一切都有所本,一切就看你如何来解梦,先创造梦境,以“奇观”破题,再细部解梦,成就一场千迴百转的寻梦曲,戏剧世界也就更加多彩多姿。

以色列导演阿利.佛曼(Ari Folman)在《与巴席尔跳华尔滋(Waltz with Bashir)》的一开场就出现了二十六只有如兇神恶煞的猛犬,一路啸聚狂奔,甚至还会对路人咆哮嘶牙,最后停聚在一座大楼前,对着站在楼顶上的主角狂叫...“为什么是二十六只?你怎么算得清楚?不是二十四五,或是二十七八?”是啊,梦中出现的数字,经过作梦的人的追述补叙,看似有了线索与脉络,却也多添了一层迷雾,观众一旦心头起了问号,就想追着了解答案,问与答的历程,其实就是《与巴席尔跳华尔滋》刻意打造的一场解梦工程。
《与巴席尔跳华尔滋》探讨的是战场上被扭曲的人性,明明不可能忘记的事物,或许因为太残忍无情或者羞愧汗颜,最后只能缩躲在记忆的角落夹层中,直到梦境来呼唤,才良心发现来完成拼图。原来男主角虽然从军,却无法开枪杀人,在执行以色列大军的登陆任务时,惊动了贝鲁特沿海村落的狗儿,齐声高吠,长官知道他无法对人开枪,于是下令要他开枪射狗,于是一枪一命,二十六只狗儿的亡灵就在枪声中飘渺升天。
人和狗不同,却同样是活生生的肉体,射狗不杀人,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主角的心理罪恶不会因为狗灵涂炭而稍有缓解,他的梦,有如狗命索命记,午夜梦迴的汗流浃背其实是想要告解赎罪,却又求救无门的业孽。

梦世界千奇百怪,超越寻常的经验法则,透过动画家的笔触,因而有了自由联想及超越自然法则的构图空间,导演阿利.佛曼光是在开场的狗儿狂崩分镜,就已经展示了动画世界比真实世界更能强力挥洒悠游的可能性,先有怪梦的影像结构,再逐一解答梦与人生的连结,一场以色列军人的良知忏情录,就让观众有了“如梦初醒”的恍然一歎。会说故事的人都懂得用梦来筑梦,《与巴席尔跳华尔滋》的导演也是梦境魔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