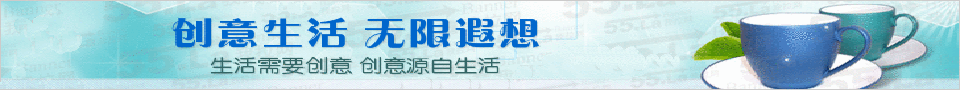

让我感到苦吧。
把我数进扁桃里去。
——保尔.策兰
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惊梦”是个诗意的情色词汇。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来源于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但观念摄影家刘铮的新作《惊梦》系列,却以一种近乎反讽的、完全剔除了色情意味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微观身体的历史记录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系列散发着罗丹《老妓女》雕塑式的美学趣味的影像群雕。我们在这群雕里能看到肥胖的女人、患有皮肤病的男人、衰老变形的女人、瘦骨伶胸的男人、散发着稻禾般生长气息的男童、浸入福尔马林已经死亡的男性等等风格迥然汇聚一堂的赤裸躯体。与时尚摄影家冯海的《游园惊梦》里被神话了的美轮美奂的青春身体相反,刘铮《惊梦》里的裸体游荡着一种记录历史的不安。这种不安不是因观看者的色情所引起的生理不安,这种不安是艺术家本人躁动灵魂的不安,更是一种太过逼近肉身的真实叙事而导致的不安。在我看来,刘铮这一系列影像的命名,至少含有三层喻意:一,刘铮在用他的影像语言给模仿《三界》的摄影新锐冯海予以最为犀利的回击。二,刘铮本人从《三界》到《惊梦》的个人惊醒。三,相对于全球泛滥以色情审美为主体的唯美摄影倾向,刘铮影像里的身体,可以说是对整个摄影界的一种警醒与挑衅。
在论述刘铮的摄影艺术的评论文章里,我们很少能看到刘铮本人的话语在评论家那里所引起的共鸣。评论家似乎只盯着刘铮的艺术品观看,而不去聆听刘铮本人的声音。图像在说话,艺术家也在说话。聆听的缺失是一种耳的缺失。这样的批评是一种聋者的批评(聋者只能重视他的目力所见)。刘铮说:“《三界》是在我拍摄《国人》中逐渐形成思路的。因为《国人》基于现实的创作,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对于传达我本人的观念存在一些障碍,为了拍摄《国人》,我走遍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有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它可以让我变得更加自由,这就是后来的《三界》包括我以后的东西,它是一种更加自由的形式。不管形式如何变化,它都是传达我的想法和我生于中国的感触。”在《国人》系列影像里,我们看到一群落后、愚昧、麻木、荒谬、阴郁的中国人的面孔。此时的刘铮显然处于对德国摄影大师桑德的模仿期。桑德大师要求自己的照片透露出这一信息:“要使自己的同胞,能在脸孔上焕发出民族血缘”。当刘铮执着于桑德这一摄影理念,诚实冷静的去记录他的同胞的面孔时,我们可以猜想到他将遭遇到与鲁迅同样的困境:他的镜头下人物的面孔是如此荒诞而不真实。这些面孔犹如戴了面具般表情单一。面具与真实的这种对立,使得刘铮无法分辨他照相机下的人物究竟是否是中国人的本来面目。刘铮很有可能被他自己镜头下的麻木面孔所震惊: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真正的心灵状态?此时此刻的刘铮才深深的意识到:他与桑德所面对的是民族品格与民族文化截然相异的两个种族。桑德从摄影家的本能出发,以影像的面孔来捕捉民族血缘记录时代的理念,显然并不适合中国。
当刘铮意识到佯装才是中国人本真的精神面目,中国人的人格实际上是一种半真半假的佯装性戏剧人格时,《三界》便诞生了。《三界》是一组穿行在现在与过去,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水乳交融的影像。这组影像微微泛黄。微黄色是一种过去色。我们看到微黄的像纸上,男性多身穿厚重的华丽戏服,女性多肉身赤裸,头上却戴耀眼的京剧头饰,他们在舞台上旁若无人的调情、性交、媾和。中国文化与戏剧的性意识一直潜藏在衣服之下,刘铮却借助影像将遮掩于层层华衣丽服下的色情文化赤裸裸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曾有媒体将之痛斥为“裸体京剧”,但这组图像显然不仅仅是媒体所理解的裸体+京剧的简单组合。它在说话,它令人不快,它喋喋不休的以视觉拍案惊奇的方式揭穿了一个一直令中国人倍感安慰的谎言: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礼仪之邦的温文尔雅不过是中国淫秽文化的一个外在假象。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而言,刘铮是中国观念摄影界的波德莱尔,他以真实与审丑的名义,无限的逼近种族文化以及被种族文化所熏陶的种族身体。《四美图》、《空城记》、《醉打金枝》、《盘丝洞》等影像皆有一种揭穿一切假象的艺术激情与扁桃般的自我嘲讽的苦涩幽默。刘铮说:“最初我是要记录中国人的心灵状态,而后却成了我自身心灵的剖析,这是我当初未曾始料的。”无需置疑,《三界》里含有刘铮本人的情欲释放。刘铮是清醒的,他知道无法摆脱自身的种族文化。他在他的种族兄弟的眼里看到了他自己。刘铮的影像作品中艺术家的自我与他者是相互交融的。刘铮即矛盾又清醒,这些苦涩的影像吟唱着与奥地利诗人保尔.策兰一样的诗句:“让我感到苦吧,把我数进扁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