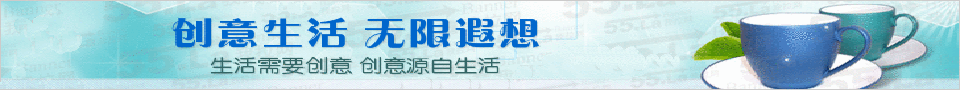埃里克·加纳案在你15岁的时候,我写信给你。我写信给你,因为在今年,你看到了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因为卖香烟而窒息身亡;因为你知道,瑞妮莎·麦克布莱德(Renisha McBride)在求助时被射杀,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只是到一个百货商店逛了逛就被枪杀。你看到,穿着制服的男人们开车撞倒并谋杀了泰米尔·莱斯(Tamir Rice)——他只有12岁,是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对象。
你看到,穿着同样制服的男人们在路边不停地殴打祖母辈的玛琳·平诺克(Marlene Pinnock)。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的话,你现在知道了,你所在国家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毁你身体的权力。这种摧毁是不是一场不幸过度反应的结果,并不重要。这种摧毁是不是源自一个愚不可及的政策,也不重要。
如果未经正当授权去卖香烟,你的身体就可能被摧毁。对试图诱捕的人表示愤怒,你的身体也可能被摧毁。走到一个黑暗的楼梯井,你的身体可能被摧毁。这些毁灭者很少会承担责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安然干到退休。摧毁不外乎是最高形式的控制,它的特权包括搜身、拘押、殴打和羞辱。所有这一切对黑人来说都很常见。所有这一切,黑人已承受很久。没有人对此负责。

玛琳·平诺克被殴打这些毁灭者身上并不存在什么独特的恶,哪怕在这个时刻来说。这些毁灭者仅仅是在执行美国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这让人很难面对。但是我们所有的说法——种族关系、种族差异、种族公正、种族化犯罪推定(racial profiling)——都在隐藏“种族主义是深植内心的体验”这一事实,而种族主义做了什么,它取出大脑、锁住呼吸道、撕裂肌肉、取出器官、粉碎骨头、打落牙齿。你不能别过脸去。你必须一直记住这种社会学、这段历史、这种经济学、这些画面、这些图表、这种全面的倒退,它们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对身体的暴力。

那个星期天,在那档新闻节目上,我试图在规定时间里向主持人尽我所能解释这些。但在片子的最后,主持人插入了一张广为流传的图片:一个11岁大的黑人男孩流着泪抱住一名白人警官。然后,她向我提问关于“希望”的问题。那时候,我知道我失败了。我记得我预计到自己会失败。我又一次困惑于自己内心涌现的悲伤。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悲伤?我走出了演播室,散了一会步。那是12月一个平静的日子。那些自诩白人的家庭正在街上闲逛。那些被当作白人养育的婴儿正坐在他们的手推车里。
我为这些人感到悲伤,也为主持人和所有在那里观看、对似是而非的希望若有所思的人感到悲伤。我那时明白了自己为何悲伤。当记者问及我的身体时,似乎她在邀请我把她从华美的梦中唤醒。我一路走来,一直凝望着那个梦。那个梦是有着漂亮草坪的完美别墅。它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野餐郊游、街区居民协会和车道。它是树屋和童子军俱乐部。那个梦闻起来有薄荷味,尝起来像草莓松脆饼。
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想逃到那个梦里去,像展开一张毯子一样用我的国家蒙住我的头大睡。但这从来不是我们的选项,因为那个梦筑在我们的脊背上,那张床是用我们的身体做成。知道了这一点,知道了那个梦是靠与已知的世界作战而存在,我为那个主持人而悲伤,我为那些家庭而悲伤,我为自己的国家而悲伤,但在那个时刻,最重要的是,我为你而悲伤。
- 评论列表(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