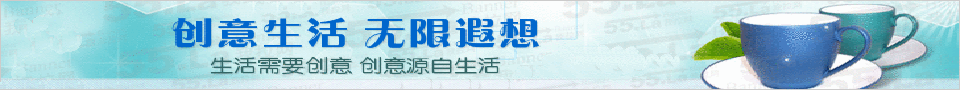
其次,现有的一些批评共识告诉我们,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日常生活批评就登场了。因为“新写实”的“新”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现实”,它是与读者置身的日常差不多同一水准的生活“实录”,即“絮絮叨叨婆婆妈妈拉家常”。“总是极力追求通俗和平易,整个叙述显得零碎而烦琐,细节事件杂多但都没有额外的特别含义,故也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只是一个接着一个散漫无绪地堆积在一起”②。就概念而论,“新写实”中的这个“新”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概念。但也不尽然,“新写实”之后,还有“先锋派小说”,之前就开始的也有“现代主义小说”。在浏览大量相关研究文章之后发现,“新写实”的“新”其实也是“先锋派”的“新”和“现代主义”的“新”。从批评中不约而同共用的一些术语概念,如“不确定性”、“偶然性”、“零散性”、“去中心化”、“意义分解”、“二元对立”等可以推知,所谓日常生活,在这三者看来基本是一回事。那么,日常生活批评,作为对“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叙事的再度审视,是不是已经丧失了一个得力的批评内视角的观照视野呢?这样的追问,当然不是求其价值标准的统一,而是说,既然三者命名不同,必然分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这无可置疑。关键是当如此等量齐观它们本来不同的日常生活观,怎么在“自在”与“自为”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过渡中植入价值?之所以哲学研究者把“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因素而加以维系,以过去为定向的领域”③,界定为日常生活,是因为一方面为了了解人们的“在家”感;同时也是为了把那些产生于传统、习惯、风俗、常识、自发的和直接的经验的图式——那些传统和惯例,改进到自为的、自觉的和自由的状态,即在更高层面解决人的不安、孤独无助和“不在家”感的问题。从这一意义来说,混判日常生活,正好不是为意义感缺失的日常生活寻找出路,反而会因批评主体意识的强烈介入,打碎乃至于搅乱了人们对那个日常的判断。像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那样,“现实”在作家那里本来已经进行了理想化、主观化装饰和修补,作家对“现实”的自我化理解之处也即是批评价值的介入之处。而特别对于像池莉《烦恼人生》这样的作品,因对“日常”和“生活”的“零度叙述”,“正是这种现实的‘还原’和本真的‘直观’中,我们获得了一种‘审美的震惊’的阅读效果”④,也意味着批评面对的正是那个既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世界”,这时,批评话语如果仍是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那一套,无异于批评功能的取消。至少也是以先在的“自为自觉”非日常生活蓝图批评“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