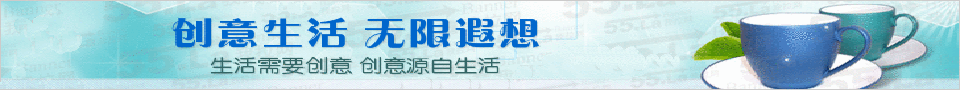
毫无疑问,理学家语录体的流行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实际上理学家本人往往都有出入佛氏的经历。但已有学者指出,禅宗的语录体流行乃是在理学家语录体流行开来之后发生的现象⑥。
其实,以“语录”著述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时尚”。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993-1059)既有文言语录,又撰有大量“口义”的著述,如《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曾问学于胡瑗的徐积(1028-1103)亦有语录(《节孝语录》)传世。石介(1005-1045)撰有《易口义》,等等。南宋晁公武(1105-1180)之《郡斋读书志》集列各种书目近一千五百种,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最为完备而著称。在这部中国目录学的大书之中,出现了很多以语录命名的书籍:如富弼(1004-1083)使虏时所录的《富公语录》(史部“实录类”)、寇瑊(?~1032)记录其出使契丹贺辽主生辰往返所见闻的《生辰国信语录》(史部“地理类”)、章谊(1078-1138)所录之《章忠恪奉使金国语录》(史部“地理类”)、李畋(生卒年不详)记录张忠定公(咏)守蜀善政的《张忠定公语录》(史部“传记类”)等。自然大量的禅宗语录也见于“释书类”之中,如《宗镜录》(一百卷)、《庞居士语录》(十卷)、《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传灯玉英集》(十五卷)、《锦囊集》(一卷)等。
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领域,出现了这么多语录体著述,确实说明了当时存在一种“以俗语为书”的时代风气。近人谢无量说:“宋时多以俗语为书者,其论学记事者有语录,杂史琐闻有平话,而戏曲亦渊源于是时。”⑦
时代风气的形成自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有宋一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此为史家所公认。谢和耐指出,11~13世纪的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相比,“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在科学文化领域,追溯经典传统,传播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技术(印刷、火药、航海技术进步、摆钟,等等),出现新哲学与新世界观,这一系列现象可比拟于西方之文艺复兴⑧。与印刷业有关的造纸、制墨、雕版工艺均有突飞猛进之发展,苏、浙、蜀、闽书坊林立,书籍印刷与流通盛极一时,宋元之际的理学家吴澄(1249-1333)《赠鬻书人杨良甫序》一文对此有生动描述:
古之书在方册,其编袠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京师率口传,而学者以耳受,有终身止通一经者焉。噫!可谓难也已。然其得之也艰,故其学之也精,往往能以所学名其家。纸代方册以来,得书非如古之难,而亦不无传録之勤也,锓板肇于五季,笔功简省,而又免于字画之讹,不谓之有功于书者乎?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尝有与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益。书弥多而弥易,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宜矣。而或不然,何哉?挟其可以检寻考证之且易,遂简于耽玩思绎之实,未必非书之多而易得者误之。噫!是岂锓者之罪哉!读者之过也。⑨
生活在这样一个印刷业、书籍流通业空前繁荣的时代之中,宋代文人与经师自身亦有切身感受,苏东坡(1037-1101)在《李君山房藏书記》一文中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⑩
景德二年夏,宋真宗(968-1022)幸国子监阅库书,问及经版情况,祭酒邢昺(932-1010)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