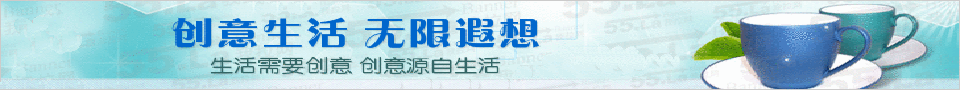
她变得头脑清醒,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除了自己,她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她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懂得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张空荡的床更让人悲伤。
《告别信》
如果上帝赏我一段生命,我会简单装束,伏在阳光下,袒露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我的魂灵。
永远说你感到的,做你想到的吧!如果我知道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看你入睡,我会热烈地拥抱你,祈求上帝守护你的灵魂。如果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你离开家门,我会给你一个拥抱一个吻,然后重新叫住你,再度拥抱亲吻。如果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我会录下你的每个字句,以便可以一遍又一遍永无穷尽地倾听。如果我知道这是看到你的最后几分钟,我会说"我爱你",而不是傻傻地以为你早已知道。
永远有一个明天,生活给我们另一个机会将事情做好,可是如果我搞错了,今天就是我们所剩的全部,我会对你说我多么爱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上帝呀,如果我有一颗心,我会将仇恨写在冰上,然后期待太阳的升起;我会用凡高的梦在星星上画一首贝内德第的诗,而塞莱特的歌会是将是我献给月亮的小夜曲。我会用泪水浇灌玫瑰,以此体味花刺的痛苦和花瓣的亲吻……
《我不是来演讲的》
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
到今天,大师及其作品既成为了我的守护神,也意味着获奖后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责任。他们获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而我获奖,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测,人如棋子,大多惨淡收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遗忘。
当代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地球是否会成为其他星球的噩梦?也许,地球只是一座从造物主手中滑落、遗留在广袤宇宙的远郊、失去记忆的村落,它没那么伟大。
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诗意的表达随处可见,另一名年轻的法国记者赞叹不已。羊羔一个劲德悲鸣,吵得孩子谁不着觉,孩子说:“简直就是路灯。”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经站过的位置。
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言语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她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摇晃着。 “你说,吃什么?”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七十五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 “吃屎。”
“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我不戴帽子,免得要在别人面前摘下来。
新鞋你要是不穿,永远不会合脚。
“只有一件东西是肯定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吃玫瑰花长大的猪,肉味一定香极了。
你要是想卖掉一件东西,就得把脸板得像去买东西一样。
(责编:wangxiao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