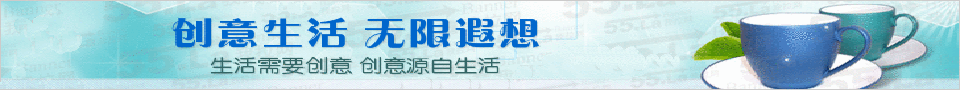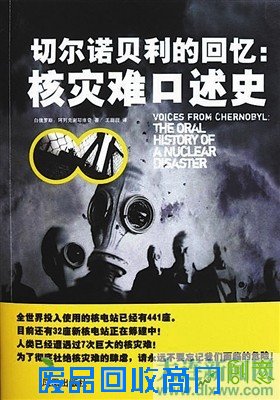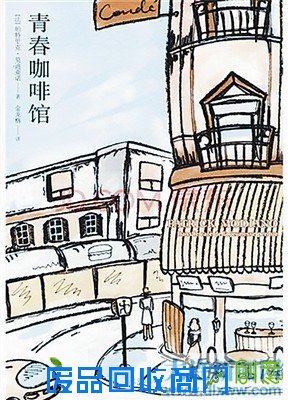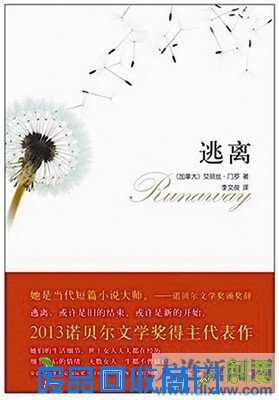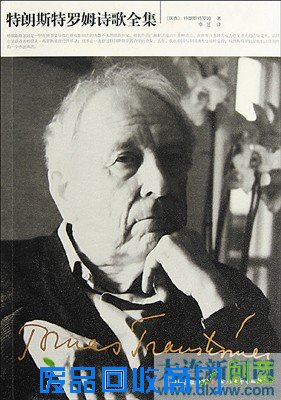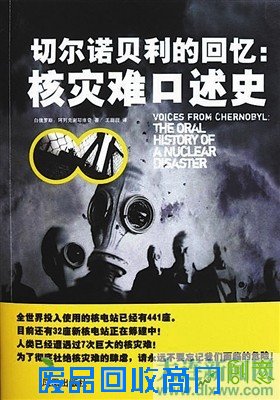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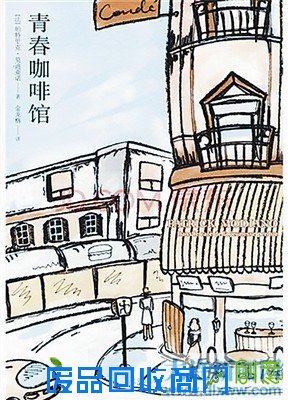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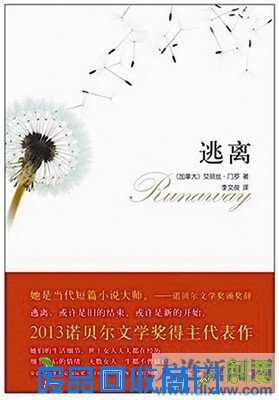
近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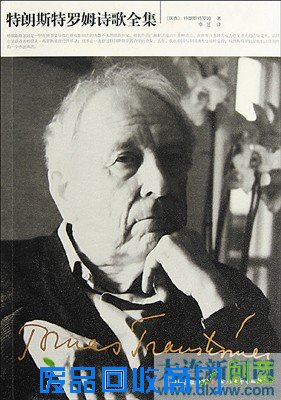
韩传喜
最近一段时间,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翻译界的极大争议,迫于各种压力,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虽然这一翻译风波已暂时告一段落,但该事件本身所折射的文学世相及其寓含的“文化问题”,却激起了更多的深层探讨。本报特邀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韩传喜为大家解读新闻背后的理性思考。
翻译伦理:
“可遵循的”与“不可抵达的”
围绕冯译本《飞鸟集》,不少评论者谈到了翻译的“信、达、雅”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文学翻译的核心所在,也是经典翻译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我们甚至可称之为翻译伦理。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尊重原著,这是“知易行难”的首要原则。译者既需要具备极高的外语水平,又需要具备准确的母语表述能力,而文学经典的译者,尚需具备对文学的敏锐感受与深刻体悟能力,同时还需要对原著产生的历史现场、作家的人生境遇与审美品格有着准确把握,这样才能做到翻译的准确到位。
事实上,相对于学术著作与科普著作,文学经典翻译的这种“信”和“达”难度更大。因为学术著作与科普著作相对比较客观理性,而文学经典,特别是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因其使用修辞手法的多样性,想象与联想的丰富性,语意与传达的模糊性,意象与意境的复合性及情境表现的复杂性……看似简洁的语句,却很难寻找到明确的意义边界,这样就使得文学经典的翻译既有“可遵循的”——翻译伦理,又有“不可抵达的”——意义边界。冯译本《飞鸟集》受到诟病,与文学经典翻译的这种难度不无关系。
同样一部文学经典《飞鸟集》,冯唐的翻译和郑振铎的翻译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至于读者的异常反响,个中原因很多,不可否认,其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在中国,能够阅读原著的读者相对较少,大部分读者是通过译本,间接地熟悉泰戈尔的《飞鸟集》的,而这种间接熟悉更多的是通过早期的译本。也就是说,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多数是借助于郑振铎的译本,建立起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的,且随着一代代读者与研究者的接受与传播,此种认知相对稳固下来。当读者看到新的译本时,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明显的陌生感,从而带来了阅读期待的受挫,在阅读接受上对其拒斥亦在情理之中。
而冯唐本身有意无意的对于原作诗句的改变甚至明显的扭曲,也是其翻译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而将这次冯式译本与原英文诗句一对照,英语基础稍好的读者,均能看得出来。
再度创造:“可同情的”与“偏执的”
文学经典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再度创造,不过必须是一种基于翻译伦理基础上的再度创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作家所身处的现实世界无限丰富复杂,作为生命个体,作家的生命体验亦是丰富多样的,因而也决定了作为其感受和观照结晶的文学作品的无限丰富性。而读者调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体味面对文学经典时,不同的对接与碰撞,必然带来更加繁复多样的阅读感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而越是优秀的作家作品,营造的意义空间越大,读者能够再度创造的空间就越大,读者与作家的跨时空遇合与对话的难度也就越大。作为特殊的读者,好的译者就是要在作家和读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不仅要与作家对话,还要借助于自己的翻译,让读者与作家对话。
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会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生发,如语意的丰富、意境的拓展、表达的润色或语言的美感追求等,从而对原著进行再度创造。事实上,面对同一部文学经典,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位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阅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也会产生某种“陌生化”的感受。译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即使作为作家的冯唐,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间,也会存在这种阻障和陌生化,甚至在某些时刻,更甚于普通读者。
文学批评中有两个术语——“同情之理解”与“偏执狂式”,这两个术语用在评价经典翻译上再恰当不过。冯译本《飞鸟集》亦是冯唐对《飞鸟集》的再度创造,这种再度创造只要是遵循了翻译伦理,就是“可同情的”。如泰戈尔诗句“The clouds fill the water cupsof the river/hiding themselves in the distant hills”,郑译本作“云把水倒进河的水杯里/他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而冯唐译作:“云把河的水杯斟满/躲进远山”。两相对照,后者的言简约而意丰厚,一个“躲”字而意境全出,比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说,冯唐作为一个当代作家,自有其优势,而这样的译作在此本中不在少数。
但冯译本中,为众人抨击的诸多翻译,不知出于何种缘由,或刻意显示自己的翻译个性;或满足自己的翻译喜好;或按照自己的审美意愿;或为了哗众取宠;或为了某种商业目的……诸多猜测都不是标准答案,但呈示在读者面前的作品,却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如何,这种“偏执狂式”的翻译,不能给予“同情之理解”,这种翻译态度也是应该引起警觉并极力避免的。
翻译乱象:“可分辨的”与“被遮蔽的”
最近一些年,文学经典的翻译颇为流行,各大出版社都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不同的经典译本。这其中包括对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翻译,也包括对有争议作家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翻译更是出版社的首选。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尘埃落定之后,图书市场必定会在第一时间推出各种译本。不可否认,这些译本中的确有质量上乘之作,但同样也有低劣粗制之作。出版社大规模出版这些译作,既有传播经典的用意,又有获取利益的考虑。为最大限度地占有图书市场,于是乎有些出版社为了多出快出,降低成本,甚至聘请一些非专业的译者,其结果便可想而知——急功近利的翻译之举必然会造成译本质量的良莠不齐。乱花渐欲迷人眼,面对琳琅满目的诸多译本,读者的选择难度明显加大了,多数普通读者难以辨识译作的优劣,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对于国外作家作品的认知。乱象丛生的经典翻译,不仅影响了读者的接受,还影响了经典的传播,尤其扰乱了经典翻译的现实生态,使得经典翻译的文学空间和市场空间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异化。质量低劣的译作随意流行,既是对经典本身的嘲弄,亦是对其“经典性”的消解。正如有论者指出,冯译本《飞鸟集》中一些极具私人化的翻译内容与翻译风格,在迎合娱乐化的文化消费心理、引发舆论狂欢的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原著的文化品格和思想意味,甚至使美好的诗意沦为恶俗的工具,这是所有的译者及所谓“文化”工作者,必须自省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冯译本《飞鸟集》引发的热议,其中既有理性的讨论,也不乏舆论的狂欢。在一个网络极其发达的时代,更多的人有了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这会促使更多的人、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和层面进入讨论,从而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观照事实;但另一方面,众声喧哗之中既有真知灼见,亦有盲目鼓噪,其结果极有可能使一次严肃的翻译之辨,演化为一场戏谑的舆论狂欢。概而观之,在这次冯译《飞鸟集》争议风波中,便不乏既没读过泰戈尔的原著《飞鸟集》,也没认真读过冯译本,仅凭几首别人摘出的诗句,便断然对译本作出是非优劣的价值判断的。对于这些判断,专业的读者也许比较容易分辨其是非曲直,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真正对他们有用的信息,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表面喧哗遮蔽了。
厘清文学经典翻译中的复杂因素,不仅关乎其本身,也关乎文学经典的传播。面对众多指责,冯唐表示:“不想回应了。让历史和文学史判断这个公案吧。”但时代的弊端不应成为自我开脱的理由。原著与翻译互为镜像的关系提醒我们,对文学经典的翻译,既要关注原著本身,亦要审视译者视域,译者的修养、品格、见地与审美水平,直接决定了文学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品质,因为它肩负着引导与推动更多的人,进一步阅读、理解、接受、传播与再创造文学经典的重任。